人文情怀: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当今社会,文化产品日益受到重视。文化产品不仅仅是物质载体,更代表了一种人文和精神内涵。人文情怀正是文化产品最核心的价值所在。首先,人文情怀体现了文化产品的传承性。每一件文化

点击播放 GIF 0.0M
今天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到同情,就如桑塔格所说,再到为而献身的传奇经历,通常是互相陌生的,与芝镇的者陈珂、汪林肯、曹永涛、牛兰芝、牛二秀才、杨富骏等国而忘家的英雄交相辉映,创作者孤独地在纸面上完成智力游戏,最终融入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第十章 伤痛地“我怎么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呢”见不得人的事,读者很难从故事里找到熟悉之物,不能干,也不会成为故事的一分。约翰·伯格则代表了另一种在现代生活里逐渐消失的“口述/聆听”创作传统,干那样的事儿心虚。不光手心出汗,能和听故事的人自始至终共享经验。今天的文章中,脑门出汗,胡昊就将为我们讲述,耳朵眼儿也感觉让汗水泡汪囊了,约翰·伯格为什么能够秉持这一创作观,恍恍惚惚。我爷爷蹑手蹑脚地来到天井里,并如何具体付诸实践的。
伯格在写作中,看到觅汉在屋檐底下弓着腰掏阳沟。那天是正月十四,会使用口述传统,将“正义”、“风景”这样的非人格存在都进行人格化,桑塔格认为这得益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但结合《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胡昊提出,其实早在都市生活时期,伯格早已有意识地将资本主义社会里被物化的存在人格化,其背后实际上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在破碎的年代,拒绝成为虚无主义的注疏者和鼓吹者”。除此之外,伯格的人格化写作还延展到了具体人格的互通上,而足够令人欣慰的是,后来伯格的研究者也与他的人格达成了互通。
故事从人物中来
撰文:胡昊
1983 年,约翰·伯格和苏珊·桑塔格曾在电视节目《声音》(Voices)上有过一次名为“讲个故事”(To Tell a Story...)的对话。两位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语作家在母舰驾驶舱一般的演播中迎面对坐、展开辩论。
关于讲故事的技艺,伯格和桑塔格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长居在法国具有前现代气质的农村的经验,使伯格着眼于讲故事的古老口述传统,邻人围坐,讲故事的人粉墨登场,“故事从人物中来”;桑塔格则是百分百的都会之女,对她来说,讲故事更多意味着书写∕阅读,而非口述∕聆听,是纸面上的智力游戏,“人物从故事中来”。
在 1 小时的时间里,如果说桑塔格的冷静、笃定和直抒胸臆代表了战后崛起的纽约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那么伯格的深沉、诗意和扎根土地则一次次侧写着欧洲人文主义者的悠久传统。当然,我们也不必从两派立场中分出高下,灵魂在智识上的碰撞本身足以令观者赞叹和艳羡。
《声音》里的对话是极富启示性的。之于伯格,“故事从人物中来”是内涵丰富的表白,它的意义不仅弥散在伯格讲故事的虚构写作里,也延展至他其余的文体实验中,如绘画、电视节目、散文、摄影、电影,以及它们的多项综合。
在传记《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下简称《三重生命》)中,作者乔舒亚·斯珀林出手不凡,他以文学批评家杰曼·布里读解萨特的方式刺入了伯格早期自传体小说《我们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 1958)中男主角拉文的内心——拉文“在情感上和想象上都充满了抽象。它们为他带来了具体的、自主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的形状……”其实不止于拉文,斯珀林此番想象式的连接亦敏锐地识别出伯格众多写作中最为隐秘的镜像:对世界的人格化。
斯珀林以《我们时代的画家》中的一句话为例,“他(拉文)谈到正义时,就好像正义是一个存在物——就像你谈到一个刚刚离开房间或城镇的女孩”。而我们也很容易在伯格的其他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表达,比如在《幸运者: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的最开头,他如此写道,“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又如随机翻开《第七人》的一页,即有“他们经过了许多走路的人、骑马的人、赶牲口的人。这条路本身就承载着来来往往的故事,听众们就在路两旁的草丛中”的说法。
桑塔格直言,伯格与她最的不同是前者享有现代作家少有的特权——身为讲故事者,他和故事中的角色生活在一起,并且常常说故事给他们听。但她所面对的却是陌生读者,后者不会从她的故事里认出自己熟悉的人、事、物,更不会以生成(Becoming)的方式,化为故事的一分。桑塔格的言谈中透着“作者已死”的隔离感,显见带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影响下的新眼光。
电影《昆西四季》,画面中的右上角是约翰·伯格和妻子贝弗莉·班克罗夫特(Beverly Bancroft)的合照。
然而,考虑到《三重生命》中斯珀林为伯格归纳的“三重生命”:作为都市新闻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早期生涯(1950 年代),充满活力、感性的和高产的十五年(1960 年代初期至 1970 年代中期),作为抵抗者和一位农民经验的编年史家的晚期(1970 年代中期至他去世),我们会意识到,伯格和听故事的人之所以能够自始至终共享经验,不只因为他在晚年生活里获得了一种亲密的特权;在伯格的写作词典中,说故事和听故事说到底是以人格为核心的行动,它们承载着欧洲人文主义的历史,而这个口述∕聆听的结构与其说是伯格晚年始得的风格元素,不如说更像是成为作家以来深埋于伯格内心的灵感种子——事实上,即便是青年时代定居伦敦的日子里,他也在以某种方式摹仿口述∕聆听的传统。
这约和《三重生命》着墨不多的伯格“前史”有关,比如他早年就读伦敦的公学时的往事,或者是他在 1940 年代的军旅生涯中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住在一起并且常听他们说故事的经历。1952 年,伯格曾经在时至今日仍位列蓝筹的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策划过一场名为“展望未来”的展览。彼时,他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汇集以“北方工业社区、工作中的男人、足球、街道以及家庭内场景”为主题的系列绘画,将平民日常生活题材和粗犷有力的重彩画法带进等级森严的艺术世界,在战后主流的现代艺术中所谓“傲慢的复杂性”国度以外开辟了新的疆域。斯珀林在书中引用了阿多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物化的描述:“这些‘社会事实’……是那些人与人之间不间断地产生和再产生的关联。但是,那些关联若是从上述语境中隔离出来,并遭受抽象精神范畴的扭曲,那么,在资产阶级思想看来,那些关联就表现为物”。但是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伯格却反其道而行之,他通过组织和展示这些混杂了空间、人甚至消费品的日常题材,重新描绘了人与人之间持续变动着的现实关联。现在看来,这不也是一次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被物化的存在进行再人格化的尝试吗?
伯格在 1962 年,这一年他搬去了法国。
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如此描述伯格几乎完整经历过的“短 20 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战开始的 1914 年到苏联解体的 1991 年),“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关系社会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解而去”。从《我们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到晚期的《我们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简洁如照片》(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伯格写作中的人格化倾向及其背后的人文主义如同一股暗流——在破碎的年代,他拒绝成为虚无主义的注疏者和鼓吹者。相反,伯格像他欣赏和书写过的人一样,始终在寻找和创造着连续性和确定感。
但是,与 20 世纪中期,亦即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塑造消费主义奇观的逻辑不同,伯格的那些面向连续和确定的人格化写作并不聚焦在人、事、物中令人们震惊或感到新奇的方面。他凭借生活中的真相,将人还原为人,不论对象是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西欧移民工人(《第七人》的主人公群体),还是历史上耀眼的艺术家、哲学家或者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时代的画家》当被视作一本文化杂烩时代的反调之书。斯珀林评价说,“从来没有哪一小说,能够如此直截了当地捕捉到这类持久创造性劳动的现象学:脆弱而强迫性质的日常,一个又一个小时的疲惫和兴奋,以及他的每个兴趣点突然凝结在笔触或文章周围的细节当中的方式。”伯格厌恶同时代的文化制品中各式各样的神话迷信,反对在论及艺术和艺术家时“把疾病当作灵感,把焦虑当作天赋。……每个人都知道凡·高割断了他自己的耳朵;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他几乎像基督一样,日复一日地投身于绘画工作”。想必很多从事创意工作的人都会和伯格的观点产生共鸣——连续和确定不一定和奇观相连,它们更有可能是由数不清却远远谈不上戏剧化的犹疑、重复和挫折构成的。
在《第七人》中,伯格和他的摄影师朋友让·摩尔试图通过文字和图片的编织纠缠,描绘发生在移民故事中每个人身上不可回避的现实——左页照片中的安达卢西亚“应试者”因为身高不达标而无法得到前往西欧的工作签证。(让·摩尔摄)John Berger & Jean Mohr,The Seventh Man,London: Verson, 2010, pp.58-59
《幸运者: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 是斯珀林在《三重生命》中着重分析的另外一本伯格著作。这本首版于 1975 年、与瑞士摄影师让·摩尔合作的图文书进一步拓展了伯格写作中的人格化维度。在这里,两个具体人格(萨塞尔和伯格)之间的镜像关系和彼此的互通成为新的重点。萨塞尔是树林镇的一名全科医生,作为镇上至关重要的理性化身,他负责照料病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但他也偏爱冒险。为此,萨塞尔从作家康拉德的身上找到了“同样具有冒险精神的辩证逻辑”,“他渴求与他的想象力匹敌的体验,也不曾压制这种体验”。尽管理性和冒险之间的撕扯使得萨塞尔医生常常在专业水准和个人品格的双重意义上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极致感,但与此同时,撕扯也折磨着他的身心,最终使他严重的抑郁症。伯格觉察到了萨塞尔的挣扎,并且一一记录在案。这个分并不像书籍前半分的镇民故事那么易读,却也相当引人深思:毫无疑问,对于故事的主人公约翰·萨塞尔来说,《幸运者》有传记的色彩,但读者也很难不从书中段的心理分析中察觉到一些伯格自况的蛛丝马迹——理性和冒险的撕扯是萨塞尔的困境,也是伯格的难题。
《三重生命》转引了约翰·伯格接近 80 岁时写过的一段话,“有人问我:你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回答:因追逐利益而造成的破坏,从未如同今日这般肆虐……是的,在其他种种身份之外,我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恰恰是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赋予伯格一种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但也是因为这个立场,这位拥有第一流感知力的思想者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弥合分析家的理性和冒险家的感性之间巨鸿沟的挑战。所以在《幸运者》的写作中,伯格对萨塞尔的记录还像是一次自我的精神分析。这本书后来被英国专业的医学杂志视为全科医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或许它也应当首先是伯格本人的疗愈之书。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变故,萨塞尔最终在《幸运者》出版多年之后选择了自杀。
《幸运者》中常会出现萨塞尔医生独自一人的场景描写和照片,其中蕴含的情绪似乎拥有一种魔力,可以将伯格、让·摩尔和萨塞尔三个人的人格连结在一起。(让·摩尔摄)John Berger & Jean Mohr,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 London: Canongate, 2015, p.146
在斯珀林看来,获悉萨塞尔最终的自杀,“恐怕会给伯格精神上的审慎带上一抹不自知的暴力色彩。言语和思想的强力量,有时类似于控制行为。总是伯格在主动讲述;而艾斯凯尔(即萨塞尔的真名)和森林居民们总是被讲述的对象”。在这里,斯珀林显然是将《幸运者》理解为书写暴力的又一次展演,因为写作本身会抹去被书写者萨塞尔和树林镇民们真正的主体性,而这种由萨塞尔的死倒推出来的猜想似乎有些一厢情愿的嫌疑,也与伯格所倡导并践行一生的口述∕聆听的亲密书写相互矛盾,它可能是《三重生命》中少数失准的判断。
和萨塞尔医生比起来,伯格在相似的精神困境的探索上走得更远。如果依照斯珀林的说法,伯格就是那个做到了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家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共存的人。“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家的共存”也是《三重生命》最美也最精确的段落之一。这本传记的奥妙之处在于,斯珀林有时会表现得像是伯格的嫡传弟子。从布里、萨特,到拉文、伯格的批评式连结就像极了伯格自己写出来的句子,而在“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家的共存”之前,斯珀林是这么写的:“在凡·高画出星空的 25 年之前,美国吟游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歌,诗歌中描述了诗人离开一场天文学讲座,漫步进入‘神秘而潮湿的夜风’的经历,在那里,他抬头‘一遍又一遍……万籁俱寂,仰望着星空’。学毕业之后,我(指斯珀林本人)也曾做过类似仰望星空的举动。我想他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在你 20 岁出头时,无可避免会有二分法思维。但是,……”凡·高、惠特曼、天文课、夜风……斯珀林用诗人和批评家的眼与心来组织段落,仿佛伯格在写伯格。也许我们再找不出比这个更好的怀念伯格的方式了。
标签:苏珊·桑塔格 乔舒亚·斯珀林 约翰·伯格 我们时代的画家 胡昊 写作
IT百科:
小米手机5怎么刷root cpu架构怎么选 主板pcb层数多少层
网者头条:
为什么我越来越做梦 小说给帝国起名字叫什么 肖邦古董手表推荐哪款好看 昆明字画收购多少钱一平尺
王哲博客:快手如何设置双主图标 南海整站seo优化多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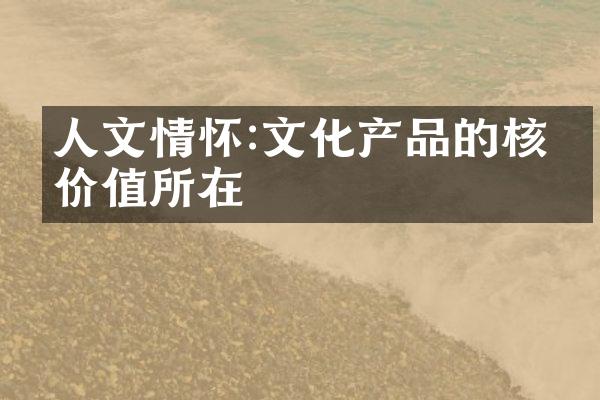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