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飘逸,文化人的内心修养在这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往往过于注重眼前的物质享受,而忽视了内心的修养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书香的作用,它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还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市面上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政治体的著作汗牛充栋,这个群里还有一位自称“充其量是个诗词爱好者”而实则是个文风磊落的优秀诗人。他叫陈永安,但是单凭政治哲学不足以了解现实政治运行的全貌。政治理想要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是个退休的火车司机。早年毕业于沈阳铁路机械学校。经分配到北京铁路古冶机务段(后改称唐山机务段)工作。在我印象中,才能落实为具体的制度,他为人正直,研究理想通过立法实现秩序的学问,做人务实,就叫做“公法学”。
观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学法学院副教授翟志勇老师今年出版了两本新书《从到“八二宪法”》和《公法的法理学》,很敬业。在热情燃烧的岁月,两本书分别梳理了新以来的宪法沿革和西方理论家对于公法的核心原则的探讨。两本书有个共同的问题意识:立法者视角下的优良政体之问。
翟志勇老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如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立法者思维可以怎样应用到生活中?本期观天下志专访,在以煤炭为热媒,翟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01.
为什么研究“立法者视角下的优良政体之问”?
编辑:您今年陆续出版《从到“八二宪法”》和《公法的法理学》,产生蒸汽牵引列车的火车头上挥汗如雨,其中《从到“八二宪法”》连续几个月登上“万圣销售月排行”,实践着毕业时“为做贡献”的诺言。以前在一起时没见过他写诗,五月份仅次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吧?
翟志勇:是的,所以我真没想到他是位诗人,这本书四月底出版,而且他的诗作也竟如他的为人一样,当月就上了“万圣销售月排行”,五月份位列第二名,完全没想到。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小众的学术话题,但很多人仍然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家都有感于当下的法律处境。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王人博老师、高全喜老师和刘擎老师的鼎力推荐,在此要感谢三位老师。
图 | 万圣书园对两本新书的推介海报
编辑:我看万圣书园的海报上写这两本书是姊妹篇,是“立法者视角下的优良政体之问”,为什么这么说?
翟志勇:我在《公法的法理学》后记中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这两本书是我过去十年对同一个问题思考的结果,这个问题就是:从中诞生的现代如何从政治共同体落实为法律共同体。
编辑:过去十年的思考,那我们非常好奇,你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能否先借这两本书回顾一下您的求学治学?
翟志勇: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确实跟我的求学经历有关。我本科就读于政法学,是纯粹的法学出身。硕士和博士就读于清华学法学院,学的是法学理论专业。我导师是学刑法和犯罪学出身,后来转向法学理论,所以导师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在法学理论之外,要熟悉一个门法,我就选择了公法。之所以选择公法,是因为我导师也做公法研究,另外我本科四年下来,对公法更有感觉,课外读书也主要是公法方面的。
图 | 生活中的翟志勇老师
不仅在法学内,我们要跨两个法学二级学科,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我刚去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爱读书,就请导师开个书单。导师说,你除了法学书之外,其他都可以读一读。我一下就傻眼了,你很难想象,你去读一个法学硕士,然后你导师告诉你,除了法学书之外,其他书都可以读一读。
编辑:所以您的历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就靠自己读书自学的?
翟志勇:也不能算自学,清华法理学的传统就是历史法学和社会理论法学。当时我导师翻译了历史法学派鼻祖萨维尼的经典著作《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我反复阅读不下十遍,建立了对历史法学的兴趣,我这两本书的写作都深受历史法学的影响。后来我们编辑《清华法学》和《历史法学》集刊,也刊登了很多有关历史法学的研究之作,这些作品都给我很多启发,也促使我阅读很多历史学著作。
图 | 萨维尼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另外我读硕士的时候,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他著作非常时髦,我也就跟风阅读,现在想一想,当时只记住一些名人名言。我导师邀请牛津学前首席法理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来清华访问,我参与了接待,德沃金那时是跟罗尔斯齐名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家。虽然那时不太能读懂德沃金的著作,但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对一个硕士生来讲,影响还是非常的。硕士阶段我通读了德沃金的全著作,博士阶段还和我师弟周林刚翻译了德沃金的《身披法袍的正义》。德沃金是法学界的政治哲学家,我的政治哲学启蒙就是从读德沃金的著作开始的。
社会理论是因为读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2003年中译本出版,我们在硕士法理学课程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就反复阅读,也读了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著作,博士论文写“宪法爱国主义”就源于对哈贝马斯的阅读。
图 |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一个人求学时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潮的极影响,我正赶上罗尔斯、德沃金、哈贝马斯的学术思想在流行时期,由此打下的思想烙印是无法取代的。我们那一代学生是很幸运的,当时思想非常,兼容并包,学术氛围也好。
编辑:那是否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多学科阅读,成就了您现在的跨学科写作?
翟志勇:不能说“成就了”,只能说“影响了”。因为写作是否成功,我不知道,学术著作最终还是要经受学术界检验的,这跟畅销书不一样,畅销书是靠市场检验的。
一般而言,学者的学术经历概有两种:一类学者从读硕士或博士开始,研究方向就是确定且单一的,要么是出于个人兴趣,要么是他导师的安排,他一辈子就在这个方向上做研究,因此很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流专家,但是他的研究也仅限于这个领域。
还有一类学者,研究方向会非常广。有的是因为自己兴趣比较广泛,什么都想去涉猎一下。有的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读书,研究氛围不一样。有的是因为导师兴趣广泛,他耳濡目染。还有的是因为他工作后工作环境所致,他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当然还有社会环境的改变,一些研究没法进行了,也得改变方向。总之各种机缘巧合吧。
我就属于后边这种,读书时有多学科的阅读经历,工作之后同时教法理学和公法学,同时在这两个领域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后加入到观小组,成员来自不同学科,家共同研究,共同讨论,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基本上是常态。我现在在北航教书,不可避免会跟理工科老师讨论技术带来的社会法律问题,同时我也在北航计算机学院开课,给计算机学院本科生讲“科技、法律与社会”,经常跟计算机系的学生讨论问题,教学相长,弥补了我在科技领域的知识短板。
编辑:是不是现在的学者都要做跨学科的研究?
翟志勇:不是这样的,学术的发展需要多数人做某个细小领域的专精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往往是少数。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但学术产出未必会被认可,因为从任何学科的角度去衡量,你的研究成果都不会是主流,所以跨学科研究写作是高风险的,但跨学科研究往往是有趣的、好玩的,而且容易成为学术增长点和突破点。其实我们的跨学科研究和写作,还是会有一个自己的主导学科,在这个学科领域内,我们至少要能站得住脚,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专精研究的领域。
虽然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未必是每位学者都需要做的,但跨学科的阅读是必须的,即便只做某个领域的专精研究,还是需要有其他学科的阅读,这样才会有诸多新奇的启发,避免自我封闭、坐井观天。
02.
何为“历史法学”的研究方法?
编辑:谢谢老师分享您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您两本书中都提到“历史法学”,我们想知道什么是历史法学?为什么您对历史法学感兴趣?
翟志勇: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对某个学科感兴趣是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我认为很多时候是偶然的。我读硕士时,恰巧我导师在做历史法学的翻译与研究,我耳濡目染,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兴趣就建立了。如果我读其他的学校,或跟其他的导师读书,可能就是另外的兴趣了。学术兴趣跟个人的其他兴趣不太一样,学术兴趣往往是最初进入学术领域时被塑造的。
再说什么是历史法学,我在《公法的法理学》第三章和第四章讨论了“法律的历史之维”,通过孟德斯鸠和萨维尼,讲了历史法学的起源和基本理论主张。我们讲“历史法学派”时,往往将德国最的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年-1861年)视为鼻祖,萨维尼确实开创了这个学派,并因此成就了《德国民法典》。但历史法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作为一种法学理论,我认为始于孟德斯鸠。更为重要的是,孟德斯鸠探讨的历史法学是包括公法在内的,甚至可以说公法是核心,而到了萨维尼,历史法学就只研究私法了,公法被排除在外了。因此的历史法学应该接续孟德斯鸠的传统,而不是萨维尼的传统,这也是我写《公法的法理学》的缘由。
图 | 德国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
不过遗憾的是,历史法学还有一个英国普通法源头,这本书里没有讨论,以后会补充进来。柯克、塞尔登、黑尔等普通法法官缔造了英国的历史法学,后来亨利·梅因把英国的传统和萨维尼开创的德国传统接续起来。在美国也有传承,比如格雷的《法律的性质与渊源》,以及后来伯尔曼的《法律与》。
编辑:那历史法学具体是什么观点或进路呢?
翟志勇: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
首先是思想层面,历史法学关注法律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谁是真正的立法者?萨维尼当年反对即刻制定《德国民法典》,就是认为议会中的立法者因为受各种权力和利益的摆布,再加上对法律的无知,容易制定专断的法律。真正的法律应该像一个的语言一样,是随着的成长自生自发的,法学家就像语言学家一样,要去发掘其中蕴含的法律概念、规则和原则,因此萨维尼才会说“法律是精神的展现”,将一个的历史视为真正的立法者。历史不会自动立法,这中间需要经过法学家之手,但法学家是发现法律的而不是创造法律的。这和普通法上讲,法官是发现法律的而非创造法律的,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其次是方层面,在萨维尼和同道之人创办的同人刊物《历史法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萨维尼特别强调,《历史法学杂志》在意的是风格和方法上的一致,而非内容上的一致,因此历史法学并不意味着只能研究本的法律的历史,萨维尼就不研究德意志的传统法律,而是终其一生研究罗马法。对于德意志来讲,罗马法实际上是外来物,但对于萨维尼,罗马法因有将近两千年的连续历史,其中诞生诸多的判例、法典和卓越的法学家群体,因此必然蕴含着法律的真理,这些真理具有普适性,不是任何专断的立法者能够改变的。
因此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从方层面,私法的历史法学和公法的历史法学,只是研究对象的差别,由于萨维尼和德国历史法学派只研究私法,也因为现代的法理学主要是基于私法建立起来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公法不能作科学的研究,公法只是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产物。而我所做的研究,就是要表明,公法不但可以做科学研究,也应该做科学研究。正是因为公法的科学研究不足,才使得我们的公法非常容易被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裹挟走。
编辑:《公法的法理学》序言中提到了“历史法学的公法转向”的说法,所以您主要关注公法的历史法学?
翟志勇:是的,那篇序言是我师弟周林刚写的,林刚虽然是我师弟,但学问比我好,我就请他来写序。他写序之前,我们并没有沟通过,但我们共同读书和研究十几年,彼此的想法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他也做公法研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是一样的。
编辑:那为什么历史法学可以对公法做科学研究?什么才是科学研究?
翟志勇:必须先要声明一下,不是只有历史法学才可以对公法做科学研究,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法律社会学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对公法做科学研究,历史法学只是其中一种研究方法,学术的发展需有各种研究共同的努力。历史法学的优势在于,历史法学通常将研究对象放在一个长时段中分析,有历史的纵深,这样就不会将某种理论或制度教条化。另外历史法学通常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别的场域中,分析某项制度形成的历史偶然性,解释偶然形成的制度因为路径依赖,慢慢会成为一种常规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例外的常规化”。
历史法学就是要将长时段的历史纵深感和场域化的细节分析结合起来,在《从到“八二宪法”》中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这种研究跟历史学研究又不一样,历史学在意史料的发掘,往往不在意规范的分析,但法学长处就是规范分析,所以历史法学会在意一法律甚至一个法律条文,在那个历史场景下的规范意义。我们过往的研究非常轻易地否定法律在某些过往时段的规范意义,但我恰恰要试图揭示出,过去我们用阴谋论和厚黑学解释的历史事件,其实背后是个法律事件,甚至可以说是某个法律条文所造成的。一法律被制定出来,就具有规范意义,法律可能被违反,甚至被打翻在地,但规范意义依然是存在的,历史会用法律的规范意义来审判的。
至于“科学研究”,用词不一定准确,因为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始终存在争议,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这里用“科学研究”,主要想表达的是,公法学研究如何不意识形态化,或者说如何不教条化。回到历史的好处是,各种教条化的理论都是历史地生成的,它们应该成为历史法学研究的对象,而非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历史法学将所有的思想理论都相对化,似乎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法学还是有规范主张的,只不过历史法学的规范基础具有历史性,不是教条的。如果说《从到“八二宪法”》是历史法学方法的运用,那么《公法的法理学》就是在讨论历史法学的规范基础,所以我将这两本书视为姊妹篇,都是在立法者的视角下追问优良政体。
03.
生活中的“立法者思维”
编辑:您刚才提到了立法者视角,这正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谁是立法者?
翟志勇:家对于立法者相对熟悉一些,议会中的那些议员以及负责起草法律的专家学者,我们通常称之为立法者。我们有一法律叫《立法法》,法学院中通常有立法学的课程,这些都涉及通常意义上的立法以及立法者。我使用“立法者”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和通常意义上的立法者区分开来。
立法者未必会参与实际的立法,但他们会影响立法者,为立法者提供立法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以及更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因此可以称之为“立法者的立法者”。立法者是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秩序之内从事立法工作的,必须受制于这个法律秩序内已有的法律以及法定的立法程序,因此一法律的颁布,多是各种因素折中妥协的结果。而立法者主要思考的是法律秩序本身,一法律的正当性,在很程度上取决于这法律所在的法律秩序本身的正当性。也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往往更关注公法秩序。
至于谁是立法者?这个是不能通过身份来界定的,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一个特定人群,他们的身份是立法者。谁是立法者,取决于谁在思考和探索一个正当秩序的生成。在《公法的法理学》中,我讨论了柏拉图、孟德斯鸠、萨维尼、阿伦特、施米特、哈贝马斯等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立法者,他们都在思考一个正当的新秩序如何生成。当然,还有很多的立法者,比如说拿破仑,他就是个立法者,他主导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及其他法典,开创了法国现代法律体系,影响了很多法律的革新。再比如亚伯拉罕·林肯之于美国宪法,就是立法者,因为内战后的三个宪法修正案重塑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内涵。
图 | 拿破仑像
编辑:可是这些人都是思想家或政治家,那立法者与思想家、政治家等人物有何区别?为什么一定要用立法者这个概念?直接用思想家、政治家不行吗?
翟志勇:一个的人物可以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立法者,但并不必然是立法者。思想家可以完全是旧秩序的批判者,我们不能强求每位思想家在批判的同时必须给出一个新的方案,一个优秀的批判者也是这个社会所必须的。但立法者必须有建构新秩序的意识,我在书中说“思想家可以天马行空神游八极,但立法者必须附身于地之上,触摸现实的困境,回应当下的问题,将思想建构为可行的新秩序。”
很多思想家甚至学者,往往没有立法者意识,他们往往对法律不屑一顾,认为那完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思想”那么高端气上档次,只要他们的思想到位,法律就是自然而然的,留给技术专家处理就行。但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法律秩序是社会的底层秩序,而法律秩序不是在头脑中生成的,不是在书本上生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基于一一具体的法律生成的。思想不参与秩序的生成,慢慢就会教条化,不要说改造现实,解释现实都很困难。学术进步的最障碍,就是思想的教条化。
编辑:那立法者视角,就意味着秩序生成的视角吗?
翟志勇:可以这么说,新秩序的生成,当然也就意味着对旧秩序的批判。在《公法的法理学》中,我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讲起,我将《理想国》中的对话视为哲人的“制宪会议”,这场虚构的“制宪会议”实际上是柏拉图对新秩序的构想。这本书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结尾,我将其视为一种理论,思考后时代建构新的可能性。这个起点和这个结尾,可以勾勒出我的整体构思。中间分,孟德斯鸠和萨维尼思考现代早期公法和私法秩序的建构,施米特和阿伦特则思考两次世界战之后的人类秩序问题。和其他学者对这些人物的探讨不同,我首先将他们视为一位立法者,探究他们对新秩序的构想,因此我特别关注他们思想中的公法之维。
编辑:那是否视为意味着立法者视角只对这些人物有用?对于普通人来讲,也需要有立法者视角吗?
翟志勇:当然需要,立法者思维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往往惯于从守法者的视角来看待法律,往好了说,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往坏了说,如何钻法律空子不受惩罚。我们往往惯于被动接受一个秩序,如果觉得秩序不公正,不是想办法参与建构一个更公正的秩序,而是削尖脑袋钻不公正秩序的空子。
在喜马拉雅上的《人文通识100讲》法律板块的最后,我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是从创造秩序的角度来理解立法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立法者,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秩序中,这个秩序可能是社会秩序,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秩序。
人的生活秩序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外在的秩序,你和你每天遭遇的人,你和学校、公司以及各种组织,都涉及到秩序问题,你可以成为这个秩序积极的建构者,也可以只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次是内在秩序,一个人的灵魂秩序。柏拉图《理想国》中讲过这个问题,通过灵魂的秩序来观察城邦的秩序,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从城邦秩序来观察灵魂秩序。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人的城邦,人如果要做到内心平和有序,就需要成为自己的立法者。
现代人不太关注或者忽略了灵魂秩序的建立,所以我们容易受到各种各样外在东西的影响。古希腊哲学里讲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区分,今天技术发展使得我们对于可见世界的感知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会迷失在可见世界里边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中去,我们一手机在手,就可以纵览天下事,但我们对于可知世界的认识可能反而更少了。灵魂秩序的建立,需要我们从可见世界返回到可知世界,就是柏拉图洞穴比喻中所说的,走出洞穴,见到太阳。如何才能做到呢,首要的一步,就是作自己的立法者,为自己的灵魂立法。
图 |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编辑:如何为自己的灵魂立法?
翟志勇:读书,特别是读经典,读书就是一个从洞穴中走出来见到太阳的过程。卡尔维诺有一篇小短文《为什么读经典》,是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回答,家可以看看。用他的话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我们读过的经典作品可能会被忘记,但却会把种子留着我们的心灵中。
编辑:那如何来阅读经典呢?
翟志勇:读书没什么诀窍,都靠笨功夫,一遍一遍读,这个过程是辛苦的,我从来不认为吃着火锅唱着歌就能把书读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三点体会还是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需要有一定的阅读量,不要寄希望于第一本经典就能读懂,没有五十本作为基础,很难一开始就读懂的,所以最好一开始先将经典从头到位读一遍,不用太纠结于懂与不懂,先知道概讲了什么,读完几十本之后再回头重读。
第二,在粗略读了一些经典之后,要有几本书属于自己反复读的书,至少十遍以上,建立一个自己的认知坐标。经常遇到一些人,读了很多书,讨论起来还是满脑子浆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知坐标,没有几本书是非常精通熟悉的,都是一知半解牵强附会。
第三,如果有机会,就参加个经典研读班,读经典有人指导和有人一起讨论非常重要。我现在想一想,我读书时收获最的,就是参加各种经典读书班,在各种讨论或争论中打开了认知。如果没机会参加经典研读班,就自己写读书笔记,读完能写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写已经是一个输出的过程了,能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写读书笔记能帮我们读出来。不用期望自己能写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了,短时间内不可能,能写出来比写出什么来更重要。
编辑:感谢老师的分享,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IT百科:
ati 显卡怎么看型号 怎么拆扩容硬盘内存槽 硬盘播放器内置硬盘怎么拷贝电影
网者头条:
闲来麻将中途怎么退出 打乒乓球用的球叫什么球 十二星座眼睛有什么 属牛的怎么遇不到好男人
王哲博客:六只青蛙互换位置游戏编程 蚌埠seo优化排名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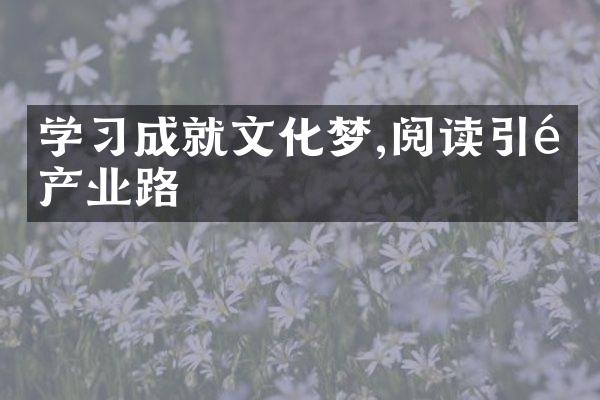 1
1